2021年12月1日下午,由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民间文学与民俗学教研室、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海外藏珍稀中国民俗文献与文物资料整理、研究暨数据库建设”共同举办的“民俗资料学:历史、理论与方法”高端学术论坛第一讲——“出土文献的民俗学价值”,通过“线上+线下”的形式顺利举行。本次讲座特邀上海大学文学院黄景春教授主讲,南方科技大学社会科学中心暨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王晓葵教授参加与谈,中山大学中文系暨非遗中心王霄冰教授主持。
黄景春教授首先从三个例子切入主题,用以说明考古出土资料的重要性。第一个例子来自黄教授求学期间面对“人彘”典故而产生的对于厕所与猪的关系的困惑,直到看到东汉陶厕所/猪圈模型文物,黄教授才明白当时的厕所和猪圈的建筑格局关系,也理解了“人彘”是把处以酷刑之人丢弃在厕所外的猪圈中。第二个例子谈论的是烟草传入中国的时间与路线。历史学家吴晗根据明清文献认为,烟草于17世纪初通过南、北三条路线传入;而出土于广西的明嘉靖中期的陶烟斗有力地表明,吸烟习俗早在16世纪中期就在中国南方流传,并且传入地仅有东南沿海一条路线。第三个例子是良渚文化和历代墓葬中所出土的玉蝉,这一器物反映了中国古老的“人死复生”观念,表现出蝉文化的悠久历史和最初寓意。由此,黄教授指出,把出土文献等考古资料纳入民俗学的视野,对于考察民俗文化的发生、演变和内涵等有着重要意义。
接着,黄教授着重以买地券为例,对“宗教性随葬文书”进行了介绍。所谓“宗教性随葬文书”,是指丧葬活动中制作并置于墓圹中的买地券、镇墓文、衣物疏等具有宗教性质的文本。“宗教性”“随葬”“文本性”是甄别这类民俗资料、理解其性质和使用语境的三个关键词。从东汉时期开始出现并流传至今的买地券(又被称作地券、地莂、地契、幽契等),则是在丧葬仪式中书写和使用的阴间土地契约,它是对地契的模仿,但具有宗教虚拟性,被用来表达给死者买地作宅、使死者得到安居之所的愿望。黄教授根据《重校正地理新书》、元刊《茔原总录》等历史文献中的买地券范文,“延熹四年(161年)锺仲游妻买地券”“黄武四年(225年)南昌浩宗买地券”“永明五年(487年)秦僧猛买地券”等十余份历代出土文献,以及他在浙江、甘肃、安徽等地田野调查中所搜集到的当代买地券,为我们解读了买地券结构化的文本内容、书写格式及其历史演变脉络,阐释了民间随葬买地券习俗所蕴含的中国民众阴间观念,即认为死是到阴间继续生活,并且这种死亡观至今仍深刻影响着国人的丧葬和祭祀方式。
最后,黄教授从民俗学研究的角度,强调了买地券的资料价值。他指出:古代文献对买地券的记载甚少;面对考古出土的买地券,考古学家仅把它们视作“古俗”,忽略了买地券在民间的传承现状;民俗学者在当代的仪式现场中发现了“活着”的买地券,但对其历史演变的状况不甚了了;只有把考古资料与田野调查资料结合起来,并参以古代文献记载,我们才能看到买地券的全貌。进而,他建议,为了更扎实地开展研究、使证据更加充分,民俗学者应当使用“三重证据法”,让多种资料相互印证,从而提高研究结论的可信性。
与谈人王晓葵教授对本次讲座的内容发表了精彩的点评和见解。王教授认为,黄景春教授关于随葬买地券文书习俗的研究,使我们了解到中国古人“视死如生”生死观的具体表现,印证了古代丧葬习俗的做法及其与当下丧葬习俗之间的关联性,并且有助于我们了解古人的经济往来。王晓葵教授还就买地券使用者的身份地位、如何通过作为偶然记录(柳田国男语)的民俗文献来建构民俗史、怎样看待同一类民俗资料在不同地域空间表现出的差异性、新文科建设背景下民俗学进入其他相邻学科并提供本学科的学识等问题,与黄景春教授、王霄冰教授展开了深入的交流。黄教授在回应时指出,古代随葬买地券的墓主是具有一定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的人;买地券的出土地点一般较为集中,并且随葬买地券习俗存在于汉族地区和受汉族影响较为深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它们往往具有书写格式、内在信仰上的一致性,我们可以在众多的偶然中发现其中的一些必然因素。王霄冰教授认为,和古文字学、古代史研究一样,民俗学利用历史和考古资料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虽然很难构建出完整的文化史景观,但我们对于古代民众日常生活的理解还是在不断地加深;在新文科的语境下,民俗学家要发挥用田野调查获取第一手资料的优势,把民俗学的研究视角带入到其他的领域,黄教授的研究是一个很好的示范。
中山大学中文堂912会议室有近20名同学、腾讯线上会议室有140余位听众参与了本次讲座,大家对买地券等出土文献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向黄景春教授请教如何辨别此类文献的价值和流传情况、买地券上的动物意象等问题,黄景春教授一一回答了听众们的提问,并推荐了买地券、冥婚习俗相关研究的一些书籍。

黄景春教授

讲座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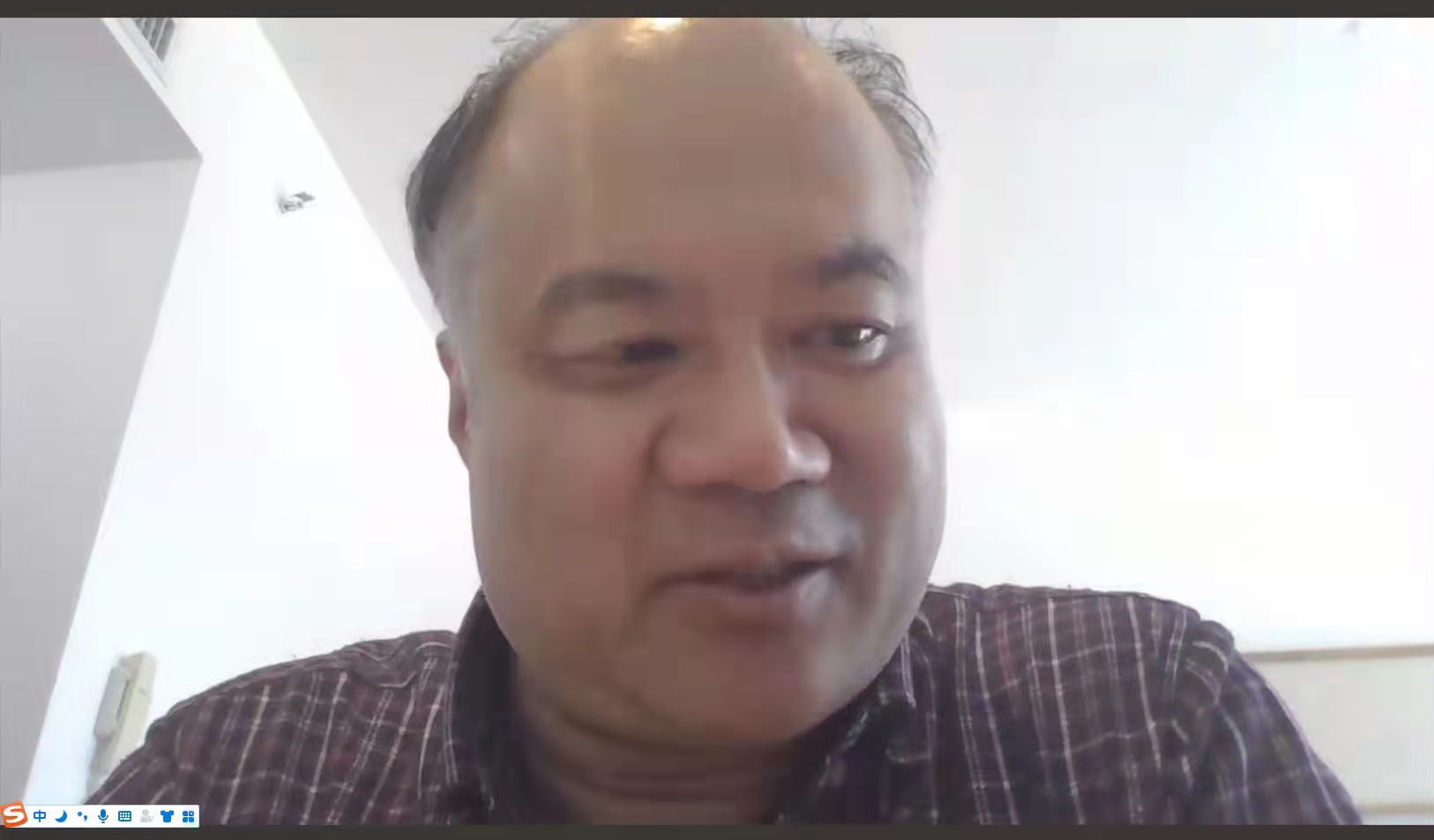
王晓葵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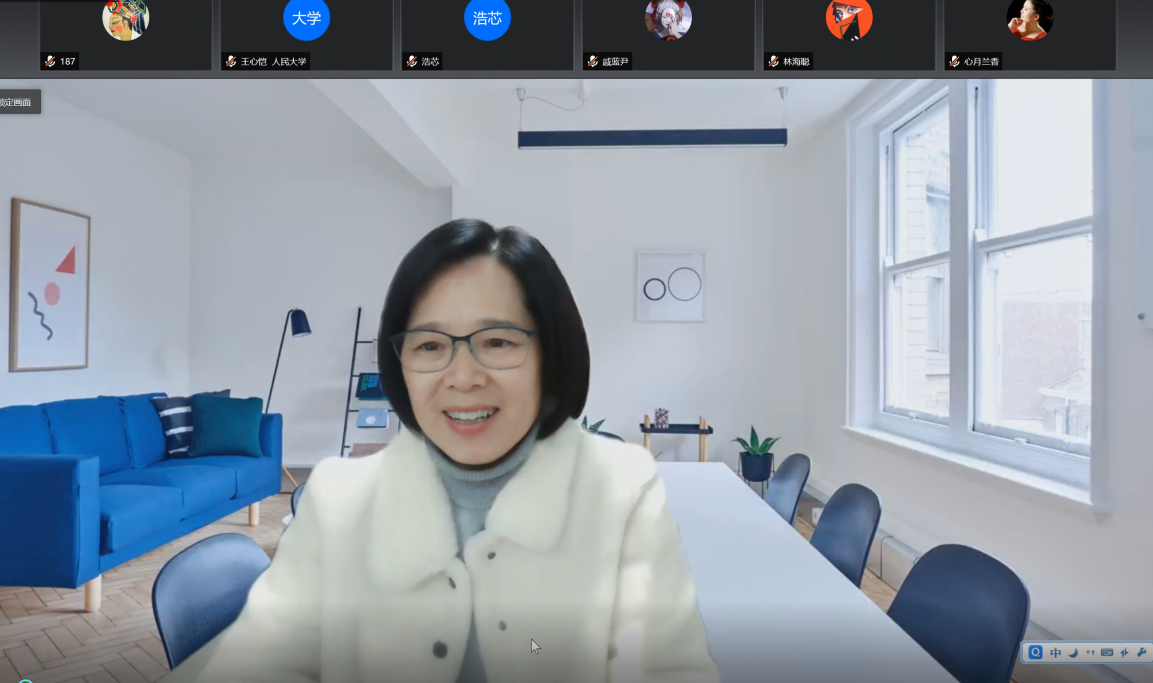
王霄冰教授

线下会场